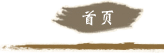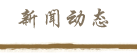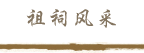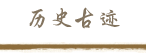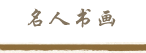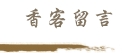人气排行榜
东 宫 变 迁
2010-09-27 责任编辑:贤良港 我来说两句
|
在贤良港天后祖祠的西南隅,蜿蜒着一条数百米的宋古码头。“潮起潮落历风雨,月圆月缺几春秋。”经年不息的潮水早已暗淡了岸边的磊石,可皎洁的明月何曾改变她千古不变的容颜……
灵慈东宫就屹立于宋古码头的东侧,与码头一同经历人间风雨、世事沧桑。陪伴“风水树”(位于灵慈东宫东侧山头的一棵三叉小树,千百年保持同样高度,被乡亲称为“风水树”。作者注)随风摇曳的身影,拥抱夕阳染红的粼粼的波纹,灵慈东宫用她仁厚、宽广的胸襟迎来了一群一群、一代又一代不辍劳作的渔夫舟子,而灵慈东宫也成了他们心中永不眠灭的“灯塔”……
一
从宫前尚存的一对宋代连柱础座及瓜楞形石柱,足见东宫有着上千年的历史。宫后“八卦井”也不知何时成了一口枯井,但它依旧静静地平躺在那里。我想:只有它们见证了古码头往日祥和而辉煌的岁月。
远航归来的渔人,经历海上风卷浪涌的颠簸,当他们踏上岸边的那一刻,他们总是有一种难以抑制的释怀——这里才是他们风雨中魂牵梦萦的归宿。于是,他们就在码头的踏足处,兴建一座宫庙,以寄托心中对土地的依依眷恋之情。
对于修建妈祖宫庙,在渔民的中间总会产生一种一呼百应的壮举,筹资、置料、动工……一切都会是十分顺利。于是一座在今天看来是那么古老的建筑就在码头的东侧屹立,一座永恒的“灯塔”也在他们的心中耸立。
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们的精神世界里就拥有了一份宁静的家园。当他们归航时,他们便向宫中虔诚地膜拜,感谢神灵慷慨的恩赐;当他们远航时,他们就在这里敬上几柱香火,再怀上一撮烟土,信心满满地启航;当休渔之际,他们就上宫前的石柱前,在心中的女神脚下安祥地修补起渔网;当岁初年末,他们就在宫前的广场上尽情地歌舞一回,祈祷来年的丰收……
于是,这群虔诚的渔民和他们的子子孙孙,就在这片祥和的港湾中劳作了一年又一年,一辈又一辈。
二
当岁月的年轮和世间的风雨不停地侵蚀他们祖祖辈辈敬仰的“灯塔”。那应该是文惠宗至正九年(1349)以后的事,就在朝廷诏封天妃父母并赐额“灵慈”之后,那群渔夫舟子的后辈们又一次把这座天妃庙好好修缮一番,并庄严地悬挂上“灵慈东宫”的匾额。
而对于他们心中的女神,他们当然就好好地打扮一番。他们给她穿上鲜艳的红袍,这在当时是“妃”才能拥有的服饰。我想:那时,在他们的心中,那祥和的神灵既是“神”又是“人”,她永远与他们同在。她就在他们的身边,她永远驻足在这片宁静的港湾,用一双安祥的眼睛佑护着他们。她与他们生生相息,永远相伴,从未分离,即使早已身处两面地,即使相隔数百年。
三
当历史的年历相继翻过,到了明代中叶,往日的码头已是艘楫穿梭,商贸繁盛。贤良港以它博大的胸襟容纳四方的渔夫舟子,码头周边的民居逐渐变的拥挤。
居住在东宫周边的黄氏家族就迁往象山西南面,他们依山开发新的居住区,面向贤良港开辟新的避风港,这就是现在的“上港”。把在这次迁徙运动中,黄氏家族的人们把他们的宗祠也移至新区,并筑造出“开山宫”面水依山地筑造新居,开辟良港,逐渐把“上港”变成“小港里”。而“灵慈东宫”就由居住在此周围的徐氏居民接下祀奉。
现在的“开山宫”与“灵慈东宫”的建筑风格相同,分两进结构,东西两侧各立一个“天井”。我刚发现“开山宫”与“灵慈东宫”的风格如出一辙之时,也深感诧异,后来听了乡亲们的诉说这段迁徙的历史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这段迁徙和礼让的岁月,足见贤良港的先祖们那种果敢的精神和和睦相处的宽容品质。从中也折射出妈祖的精神博大和仁厚。其实,妈祖的精神也是在人们一次又一次的迁徙之中传播得以发扬的。我们的先祖由于种种原因,为了生存,为了生命的繁衍,他们总会面临迁徙的抉择。当他们到过一个新的居所,他们总会带上自己精神瓣寄托——神灵来保佑一方平安,庇佑吉祥安宁。而妈祖就以她仁慈博爱的胸襟,迎合人们的精神寄托,成为人们真正的精神港湾。
四
清康年间,为了实现台湾的统一伟业,贤良港的乡亲举家迁徙到“界内”,散居涵江等各个角落。“灵慈东宫”就孤寂地矗立在岸边。我不知道当时的台湾渔民到达这神圣的地方,是怎样的一种举措,而关于那段岁月的回忆,人们的脑中早已模糊不清。
在复界后,码头和东宫周边变得更为繁荣了,在人们的记忆中,只有那繁华似锦的岁月,王朝,此时屡屡褒封妈祖,台湾周边也纷纷踏上这座“精神家园”,“心灵源泉”码头上迎来了一群群来自海峡对岸的血肉相连的同胞,他们一同在共同敬仰的女神脚下膜拜,共同携手去乘风破浪,去披荆斩,共同开创灿烂辉煌的“康乾盛世”。
五
直至1974年,前往湄洲岛的航线改为从文甲出发,东宫和古码头才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我不知道,从繁华到宁静是怎样的一种际遇。但如今的东宫依旧屹立在古码头的东侧,用它的一砖一瓦,一石一土向世人讲述过去的点点滴滴,倾诉世间的风风雨雨,述说历史的一幕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