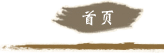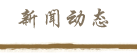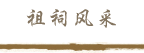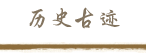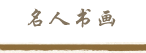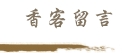人气排行榜
里籍地不等于出生地
2012-04-28 责任编辑:贤良港 我来说两句
|
-----与陈均先生商榷
妈祖诞降于莆田湄洲湾贤良港(今秀屿区山亭乡港里村),这原本是清代邑人林清标《敕封天后志》中所确认的。他是综合了《天妃显圣录》等史料记载、实地考察,尤其是台海信众的妈祖信俗之后,才作出这一明了判断。
千百年来,广大妈祖信众都把到天妃故里贤良港“娘家”上香朝拜,作为一项重要的妈祖信俗活动,代代传承。正如莆田妈祖研究先行者、地方文史专家肖一平先生1987年8月出版的《海神天后东渡台湾》一书所言:“妈祖的远祖,九牧六房林蕴宗祠在莆田城内,亦陪祀妈祖。妈祖生父母祠在莆田忠门乡港里村,祠内陪祀妈祖及其兄姐神位。每遇妈祖节日,妈祖祖庙的出巡妈祖必到以上各祠谒祖,即所谓妈祖‘走娘家’,当地林姓宗亲例必举行大规模的迎驾活动。”明永乐十九年朝廷派内官修整天后祖祠后,香客就有了先到天后祖祠朝拜后再往湄洲祖庙进香,进而形成“妈祖走娘家”的习俗。至康熙五十九年,奉旨天后本籍宗祠令地方官春秋谕祭载入祀典后,风气更盛。莆仙、惠安、晋江一带的天后宫每年进香都遵俗先到贤良港。
“妈祖走(当代称“回”)娘家”的习俗,并非近年新闻炒作作秀的产物,而是源远流长的文化积淀。且举两个最著名的明清“走娘家”事例,以证明“古之人不余欺也”。(苏轼《石钟山记》)
莆田荔城区新度镇锦墩妈祖宫,每逢闰年都要举行“妈祖探母”活动。每次均组团数百人,在古时交通不便的情况下,都是步行往返。其起因是:宋元时代,该村有位徐姓信婆得知贤良港有个少女姓林名默,因救父寻兄而得孝深受感动。信婆为了取孝回乡授教后人,便只身步行数十里来到贤良港祖祠,在三月二十三妈祖诞辰那天把妈祖神像请回本村奉祀。临行前,信婆举香三炷许诺:“逢闰年这天都要送妈祖回故里探亲。”此后,每逢闰年的前夕,便成为该地信众举行“妈祖探母”的活动日,一直延续至今。
在贤良港祖祠内的大门顶,悬挂一块题有“灵通龙井”四个大字的古匾额。此匾是古代仙游度尾潭边龙井宫赠送的。龙井宫建于清初,现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其妈祖大殿两旁板楹对联“神灵同仰女中圣,利济不遗天下人”,是清朝御史江春霖所书。宫内奉祀的妈祖被民间尊称为“玉姑”,且流传着“玉姑探亲”的神奇故事。即该宫大门前西侧有个“龙井”。井中有十二尾神鲤,平时沉在水中很少出头露面。但每到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妈祖诞生日来临前夕,这十二尾神鲤同时浮出水面,头朝向贤良港方向,以示妈祖要回娘家探亲。当信众护驾妈祖神像往贤良港行走时,这十二尾神鲤便又同时沉下水中,不见踪影。传云是“贤良港祖姑神灵在龙井的现圣”,故有“灵通龙井”之典故。后来,所在民众把这“灵通龙井”四字,制成匾额悬挂在妈祖故乡贤良港祖祠大门顶,作为该村世代信众每年护驾祖姑前往贤良港娘家“探亲”的历史物证。
由于该宫距贤良港较远,且古代交通不便,每年举行妈祖回贤良港“探亲”活动的信众,须步行三天三夜方能到达。因此,途中还要在忠门“月埔”等地过夜。一路上,玉姑所经过的乡村,信众们纷纷举香迎送,非常热闹。
试问,倘若贤良港不是天妃故里、“父母之邦”,哪能获得如此荣光?倘若不是严格依此礼仪程序办事,那么长幼尊卑之先后次序不是完全“乱了套”吗?
不过,也有一些人士不合时宜地提出质疑,予以否认。2006年,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会长陈钧先生在《妈祖生地家世考》一文中就提出:其一,“妈祖出生贤良港,这是林清标的一大误会”,是“差错”与“篡改”;而“目前所见的众多典籍,均持‘妈祖出生于湄洲屿’说,看来是十分明确的,不存疑义”。其二,“妈祖出生于贤良港。清代以前的所有典籍,均无此记载。只有清高宗乾隆时期的林清标在《敕封天后志》中,才开始这么说的。”
然而,陈钧的这样两个结论未免失之草率。
只要审察他所引证的共计66则古今材料,就不难发现,他的前提与结论之间,并非必然性推理,而仅仅是或然性推断,其推理结论超出了前提的断定范围。限于篇幅,笔者不能全部加以重复引述,只能摘其有代表性之要者陈列如下(序号为笔者所加,原引文、时间、人名等错处连连,硬伤明显,顺便一一予以订正说明):
1、妈祖出生地址最早的文献记载,是南宋特奏名进士宋廖鹏飞,于宋高宗绍兴二十年(公元1150年正月十一日)撰写的《圣墩祖庙重建顺济庙记》,其中明确指出:“世传通贤【笔者按:应为“通天”】神女也。姓林氏,湄洲屿人。”
2、李俊甫在南宋宁宗嘉定二年(公元1209年),撰《莆阳比事》卷七称:“湄洲神女林氏,生而神异,能言人休咎。”
3、莆田人丁伯桂在宋理宗绍定三年(公元1230年)【笔者按:应为绍定二年】撰《艮山顺济圣妃庙记》:“神莆阳湄洲林氏女,少能言人祸福”。
4、李丑父宋理宗淳祐十一年(1251)【笔者按:应为开庆元年(1259)】所撰《灵惠妃庙记》:“妃林氏,生于莆之海上湄洲,洲之土皆紫色”。
5、黄岩孙在宋理宗宝祐五年(公元1257年)撰《仙溪志·三妃庙》称:“顺济庙,本湄洲林氏女”。
6、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莆田籍文学家,生于宋孝宗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卒于宋度宗咸淳五年(公元1296年)【笔者按:应为1269年】,曾官拜工部尚书和侍读,又以龙图阁学士致仕的刘克庄,他在《题莆田白湖庙》【笔者按:应为《白湖庙二十韵》】诗中更加明确地指出:灵妃一女子,瓣香起湄洲。这两句诗概括了妈祖由人变神的史实,并点明妈祖出生在湄洲,妈祖信仰肇自湄洲。
7、莆田人黄四如【笔者按:笔者按:应为“黄仲元,号四如”】在元成宗大德七年(公元1303年)作《圣墩顺济庙新建蕃釐殿记》中说:“妃族林氏,湄洲故家有祠”。
8、黄向在《天妃庙迎神》中述:“天妃者,兴化军莆田县湄洲林氏女”。(载明·李翊《续吴郡志》)。
9、元文宗在天历二年(公元1329年)的《御祭文》中云:“惟乾坤英淑之色,郁积扶舆,外笃生大圣,炳灵于湄洲”。(载《天妃显圣录》)
11、成书于元代的《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四《天妃娘娘》称:“妃姓林,旧在兴化路宁海镇,即莆田县治八十里滨海湄洲地也。母陈氏,尝梦南海观音与以优钵花吞之,已而孕十四月,始免身得妃。”
12、张翥在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前的《圣妃灵著录》云:“妃莆田人,都巡检林公愿第六女,母王氏,于宋建隆元年三月二十三日生妃于湄后林之地。”
13、明成祖朱棣在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撰的《天妃颂》,首联就是:“湄洲神人濯厥灵,朝游玄圃暮蓬瀛”。【笔者按:经查,永乐皇帝此诗是附于《御制弘仁普济天妃宫碑》文末尾,作于永乐十四年(1416)四月初六日。碑石今存南京静安寺。】
14、李贤等奉敕在明英宗天顺五年(公元1461年)修的《大明一统志·兴化府·莆田县》载:“天妃庙在湄洲屿,妃,莆人,宋都巡检林愿之女。生而神灵,能言人祸福,殁后乡人立庙于此。……本朝洪武、永乐中,凡两加封号。”
15、黄仲昭在明孝宗弘治四年(公元1491年)修《八闽通志·天妃庙》中称:“在新安里鯑江湄洲屿上,其神即弘仁普济天妃,今庙盖其故居也。”
16、周瑛在明孝宗弘治十六年(公元1503年)的《兴化府志·户纪·湄洲屿》叙述:“湄洲在大海中,与极了相望。林氏灵女今号天妃者,生于其上。”
18、陈让在明世宗嘉靖二十二年(公元1543年)修的《邵武府志·天妃宫》云:“神姓林,世居莆阳湄洲屿,巡检林孚第六女也。”
19、明人黄光升在明穆宗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撰《泉州府志》中指出:“神居莆阳之湄洲屿,都巡检愿之季女也。”
20、康大和在明神宗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的《湄洲屿》中称:“在大海中,林氏灵女号‘天妃者’,生于其上。”在《天妃》中又云:“天妃之神本姓林,世居莆阳之湄洲屿”。(载明·万历《兴化府志》)。
21、陈琯在明神宗万历十九年(1591年)修的《宁德县志·灵慈庙》云:“神姓林,世居兴化府莆田县之湄洲,闽王五审知统军兵马使林愿第六女也。”【笔者按:应为“王审知”】
22、黄凤翔在明神宗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修的《泉州府志·天妃宫》中称:“神本姓林,世居莆阳之湄洲屿。”
23、周婴在明神宗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的《湄洲天妃宫碑》称:“天妃者,湄洲山中之神女也,姓林氏。”(载《远游篇》卷九)。
24、林尧俞在明神宗万历四十三年的《兴化府志·湄洲屿》云:“一名鯑江……在大海中,与琉球相望。天妃庙在焉。洪武、永乐中两加封,香火甚三蹙。庙其故地也。”【笔者按:引文有误,应为“……洪武、永乐中两加封号,香火甚盛。庙其故居地也。”】
25、何乔远在明神宗万历四十三年的《闽书·方域志·湄洲屿》中称:“一名鯑江,在大海中,与琉球相望,顺济圣妃庙在焉,妃姓林,唐闽王统军兵马使愿之女上人也。始生而地变紫,幼通悟秘法。”【笔者按:引文有误,应为“顺济天妃庙在焉。妃林姓,唐闽王时,统军兵马使愿之女,上人也。”】
26、张燮在明神宗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的《东西洋考·舟师考勤·祭祀》中云:“天妃世居莆之湄洲屿,五代闽王时都巡检林愿之第六女也。”
27、成书于明熹宗天名(公元1621-1627)年间,题为丘人龙编的《天妃显圣录·序》称:“天妃生于湄洲屿,道成飞升,屡显灵异。”【笔者按:“天名”应为“天启”。再则,《天妃显圣录》初刊于康熙十年(1671)左右。引文亦有误,应为“天妃生于湄屿,道成飞升,屡显神异”。】
28、林登名在《莆舆纪胜·湄洲屿》云:“天妃,都检林愿第六女,母王氏,世居莆之湄洲屿。”
29、伍瑞隆在明思宗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重建大榄天妃庙碑记》中称:“天妃本莆田之湄洲人,都巡简(检)林愿之第六女也。”(载清·光绪《香山县志》)。
30、无名氏在明代刊行的《搜神记》卷六记载:“天妃,三月十十三日生,妃,莆人,宋都巡检林愿之女,生而神灵,能言人祸福,殁后乡人立庙于湄洲之屿。”
31、费元禄在《天妃庙碑》云:“天妃林氏……旧在兴化军宁海镇,而【应为“即”】莆田县治八十里滨海湄洲地也。”(《甲秀园集》卷三十六)。
35、僧照乘在清圣祖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笔者按:应为康熙十年】正式刊刻的《天妃显圣录·天妃诞降本传》云:“天妃,莆林氏女也……曾祖保吉公……弃官而归,隐于莆之湄洲屿。”
38、郁永河在清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在《海上纪略·天妃神》中称:“相传神为莆邑湄洲东螺村林氏女,自童时已具神异,常于梦中飞越海上,拯人以【笔者按:原文为“于”,否则不通】溺。”
39、陈梦雷等奉敕编纂在清圣祖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706年)完成的《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八:“按《莆田县志》:天妃林姓,世居莆之湄洲屿,五代闽王时都巡检林愿之第六女也。”是书《职方典·兴化府部》亦有同样的记载。
40、徐葆光在清康熙五十八年(公元1719年)撰写的《天妃灵应记》中写道:“天妃姓林氏,莆田湄洲人。宋都巡检林愿第六女。”(载《中山传信录》卷一)。
41、禅济布于清世宗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在《为请赐天后祠匾额事奏折》云:“经臣施琅恭疏具题,圣祖仁皇帝敕建神祠于其原籍莆田县湄洲。”(礼部题本同上)(载《清代妈祖档案史料汇编》第3页)。
42、郝玉麟等在清世宗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题写的《为请颂闽省南台匾额并立礼典事》中称:“……默相王师功成底定,敕建神祠于原籍莆田湄洲地方”。(礼部题本同上)(载《清代妈祖档案史料汇编》第42页)。
43、尹士俍在清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修的《台湾志略·寺庙旧迹》载:“按天后,乃宋巡检林愿女,住莆田之湄洲屿,幼与神异,能预知人休咎。”
46、王必昌在清乾隆十七年(公元1752年)修《台湾县志·天后》云:“天后姓林,世居莆之湄洲屿。父名愿,五代时官至都巡检,即邵州刺史忠烈蕴公之玄孙也。”【笔者按:引文有误,应为“天后林姓,世莆田之湄洲屿。……即邵州刺史忠烈蕴之玄孙也。”】
47、廖必琦在清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修的《莆田县志·天后》中称:“天后姓林。世居莆之湄洲屿。”【笔者按:引文有误,应为“天后林姓,世居莆之湄洲屿”。】
48、清高宗在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敕撰《大清一统志·兴化府天妃庙》载:“宋天后,世居莆之湄洲屿。宋都巡检林愿第六女。始生时地变紫,有祥光异彩。”
54、刘业勤在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的《揭阳县志·天后庙重建碑记》称:“考神世居莆阳湄洲屿。”
55、清乾隆皇帝在乾隆四十三年颁发的《着福建督扶嗣后于天后本籍春秋致祭并载入祀典上谕》:“天后神庙屡著灵应,而福建湄洲系神原籍。”(载《清代妈祖档案史料》第110页)。
56、赵文楷在清仁宗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的《加封天后“垂慈笃佑”四字命臣文楷于福州致祭礼成恭祀》:“有宗开基日,惟神诞降年。普陀现前世,湄屿应高躔(原注:湄洲屿,天后诞降之地)。”
58、吴裕仁在清仁宗嘉庆八年(公元1803年)的《惠安县志·天后宫》云:“后父讳愿,后其第六女也,世居莆之湄洲屿。”
59、陈寿祺在清宣宗道光九年(公元1829年)《重纂福建通志·天后传》云:“后姓林,世居莆之湄洲屿,宋都巡检林愿第六女也。”【笔者按:引文有误,应为“后林姓”。】
62、杨峻【笔者按:应为“浚”】在清德宗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湄洲屿志略》中叙:“湄洲在大海中,与极了相望,林氏灵女今号天妃者,生于其上。”
63、《福建省志·天后传》载:“后姓林,世居莆之湄洲屿,宋都巡检林愿第六女也。”(载《妈祖图志》)。
64、《台湾神像艺术·天上圣母—妈祖》称:“天上圣母妈祖的俗身,系福建省兴化府莆田县湄洲屿人,姓林,名默娘。”
65、台北云龙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华夏诸神—妈祖卷》的“导言”中写道:“妈祖确有其人,姓林名默,祖籍福建省莆田县湄洲屿,生于北宋建隆元年(960年)。”
66、近年由湄洲祖庙董事会、湄洲妈祖文化研究中心编印的、由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题名的《妈祖》,明确写道:“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农历三月廿三,妈祖这位神奇的女子降生在湄洲岛。”
陈钧在以上引述之后归纳道:“目前所见的众多典籍,均持‘妈祖出生于湄洲屿’说,看来是十分明确的,不存疑义。”
可惜,如此“霸王硬上弓”的结论未免下得太早。把立论建立在种种错抄误读的历史资料和历史叙述的基础上,既经不起推敲、验证,也会误己误人误社会。进行史学方面的学术讨论,最基本的前提是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真实。不能生吞活剥、张冠李戴,更不能搞莫须有和想当然。实际上,上述引证,明确说妈祖出生在湄洲屿的,仅有周瑛等6条(即第16、20、27、56、62、66条,其中一条还是注解),即只占十一分之一,并非什么“均持此论”,而是属于少数派;绝大多数史料,只不过言及妈祖为“湄洲屿人”、“莆田湄洲人”、“湄洲山中之神女也”,或曰“世居莆阳湄洲屿”、“原籍莆田县湄洲”,还有曰“炳灵于湄洲”、“天妃庙在湄洲屿”等等。
笔者特地依据1989年蒋维锬先生编校的《妈祖文献资料》,其中所列的宋代有关妈祖的诗文作者16人(廖鹏飞、黄公度、宋光宗、赵师侠、洪迈、宋宁宗、陈缚、李俊甫、吴自牧、丁伯桂、刘克庄、真德秀、李丑父、黄岩孙、祝穆、潜说友),没有一人一篇明确认定天妃是生于湄屿的,而并非陈钧所谓的宋代6条记述“所记载的都说妈祖的出生地在湄洲”云云。而绝大多数记载,也只是说明湄洲屿是妈祖的世居地,湄洲屿是妈祖庙宇所在地等等。
再请看看陈钧先生自己特别得意,注重说明的三条引证吧。
其一为第60条:莆田人陈池养在清宣宗道光十年(1830)前后,所写的《林孝女事实》记叙:“林孝女系出莆田,唐邵州刺史蕴九世孙。曾祖保吉,周显德中为统军兵马使,弃官归隐湄洲屿。祖孚,袭勋为福建总管。父惟悫为宋都巡官。孝女次六,其季也。生弥月不啼,因名曰默。”陈先生引述后,马上紧接着说道:“此处明白无误告知,妈祖林默出生于‘湄洲屿’。”
其实,明眼人不难分辨,陈池养所讲述的只是妈祖的嫡系家世源流:“曾祖保吉……弃官归隐湄洲屿”,怎会推延解读成什么“明白无误告知,妈祖林默出生于‘湄洲屿’”呢?
应该提醒一下,陈池养在同一篇文章中,还明确指出林孝女(即林默)乃“海滨之人”,并非岛屿之人也。为什么陈钧先生视而不见呢?
其二是陈钧先生认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第6条刘克庄《题莆田白湖庙》诗中的两句“灵妃一女子,瓣香起湄洲”,更加明确地“点明妈祖出生在湄洲”。
其实亦不然。“瓣香”一词,原系佛教语,带有“师承、敬仰”之意。如宋代陈若水《沁园春·寿游侍郎》词:“丹心在,尚瓣香岁岁,遥祝尧龄。”清代计东《再与宋牧仲书》:“乃於郡署旁废圃中,西向设瓣香,流涕再拜而去。”因此,这两句诗说明“妈祖信仰肇自湄洲”尚可,倘若由此认定“点明妈祖出生在湄洲”则未免太过穿凿附会了。
其三为第13条:明成祖朱棣在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撰的《天妃颂》,首联就是:“湄洲神人濯厥灵,朝游玄圃暮蓬瀛”。“再次明确妈祖生在湄洲”。
经查,明成祖朱棣这首诗是附于《御制宏仁普济天妃宫之碑》文后,作于永乐十四年(1416)四月初六日。碑石今存南京静安寺。开头的这两句翻译成白话大致为“湄洲神人(指天妃妈祖)其威灵显赫,早上巡游于昆仑山顶的玄圃,夜晚又能抵达海上仙山蓬莱瀛洲。”这样两句诗怎会“再次明确妈祖生在湄洲”呢?笔者再三通读了全诗的24个句子,依然怎么也“明确”不了“妈祖生在湄洲”。
如此囫囵吞枣、不求甚解的误读引证,能得出什么科学正确的、令人信服的结论呢?
那么,陈钧所引述的几条认为妈祖生于湄屿的说法,又该如何辨析呢?
通过进一步的仔细辨析不难发现,除周瑛外,其余均未必可信。而周瑛《兴化府志·户记·湄洲屿》所述:“湄洲在大海中,……天妃者,生于其上”,仅仅是一句判断,并无任何阐述,实属语焉不详,难成确证。
杨浚《湄洲屿志略》中所言,实际上只是原原本本、一字不改地转述周瑛《兴化府志·户记·湄洲屿》所述,并非确证。因为杨浚在同一本书的“世系图”中,又认为林默曾祖林保吉“弃官隐贤良港”,并且到贤良港妈祖祖祠实地考查,然后郑重其事地写下如下文字:“按:愿为神太高祖,非父也,各书记载多误,神父实名林惟慤,兹据祖祠神主并族谱更正之。”
再则,杨浚在该书付梓前夕,在书序末尾附上一首五言排律,赠給赞助其出书的“唐蓉石前辈”,其中有这样的诗句:“笄珈参吉蓼,俎豆祀怡山(怡山院为天妃宫,位于福州马尾亭江镇亭头村怡山麓)。古井仙官集,前身大士班。千丝治泽国,一脉笃乡关。……鯑江过客拜,螺港使臣还。”字里行间,湄洲岛与贤良港相提并论的情愫溢于言表。
康大和一会儿说“生屿上”,一会儿又说“世居莆阳之湄洲屿”,属摇摆不定、模棱两可者。
丘人龙所作的《天妃显圣录·序》中,为什么会称“天妃生于湄洲屿”呢?我想可能有两个因素使然:其一,他是受湄屿僧人照乘所托,整理、编辑《天妃显圣录》的;其二,据蒋维锬先生推测,“寄寓郡城”的丘氏“很可能是湄洲人”。受人之托,加上家乡情结,美言一句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应该指出的是,丘氏的这篇序言,1685年林麟焻作序出版修订本时,已经撤销了——并且“不见于后来的任何一种改编本”。其中缘由是否因为,前后6位作序者,仅有丘人龙一人声称“天妃生于湄洲屿”呢?
至于近年由湄洲祖庙董事会主编的宣传材料所载,按照惯例,不足为据。
总之,陈钧先生所犯的逻辑推理错误是十分明显的。众所周知,说某人“世居”某地或是“某地人”,并不等于他一定是出生于某地。也就是说,籍贯、世居地、升天处、庙址等等,跟人物出生地二者之间,是不能够划上等号的——这应该算是日常生活基本常识吧?
可见,真正“误会”历史、误读史料的,正是陈钧先生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