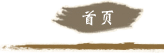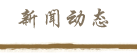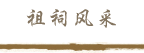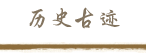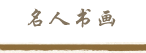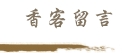人气排行榜
我陪台湾教授去考察
2012-10-11 责任编辑:贤良港 我来说两句
|
——台湾“清华大学”古明君教授来妈祖诞生地贤良港调研
9月10日由莆田学院曾伟老师陪同台湾“清华大学”古明君教授来妈祖故里贤良港做有关妈祖历史文化的调研和考察。为了力求真实性,要在这边做为期5天的考查。我受祖祠董事会委托,有幸地陪同她们去进行采访。后因曾伟老师有事回莆田,就只有我和古教授同行。
第一站;晚上去我奶奶家,见了面客套之后,就开始了采访,〈由于言语不便,由我作为翻译〉一开始古教授问了些解放以前的事,比方说:有没有祭祀妈祖?要怎么祭祀?在那个吃都是问题的年代,都用些什么供品?妈祖怎样换衣服的?要有那些忌讳?在文革时有没有去祭祀妈祖?文革中有没有人去问妈祖卜杯?祭祀的钱谁出?祖祠是什么时候重建的?哪来的钱?
我奶奶回答是:一直以来都有祭祀妈祖,那是老祖宗传承下来的。过去没有钱买高贵祭品就煮几个鸡蛋,染成红色,用黄豆做豆腐在炸成豆腐皮,再用自家土地生产的花生,或用小麦做些粿品,还有就是茶酒了。妈祖换衣服时要用艾蒿和桔子叶煮开的水,毛巾和脸盆要全新的,给妈祖换衣服的人也要有一定的资格〈要三代同堂,必须要有男孙子了,还必须是伺候妈祖有一定年限〉在换的时候也不能有闲人观看,要用帘子挡住,两个换,一个端水,放鞭炮〈那个端水放鞭炮也没资格看〉要洗的时候先放鞭炮,洗好了也要再放鞭炮。一年只换洗一次,时间一般在妈祖诞辰前夕,日子要挑双日,单日不行。文革时但凡妈祖诞辰和升天日才会偷偷去祭祀。也不敢大白天去祭祀,都是等天全黑了,要不就是天没亮的时候。文革时没有卜杯,是不敢,怕被人发现〈因为宝像被发现是要充公投炉的〉。祭祀的钱按户摊,花了多少算了下,由林氏子孙出钱。说起重建祖祠的话,奶奶泪流满面,不断的重复着,“妈祖落难了,要不是有我们几个老太婆护着,你们现在也就看不见这尊从南宋传留下来的宝像了”。为了重建祖祠,她们挨家挨户收钱,一毛,二毛,三毛``````实在没钱了就收花生啊,黄豆之类,在拿到外面去变卖,历经几年才竣工,那真是没钱重建起来的。
古教授也有问些琐碎的,比方说解放前坐月子是吃什么的?解放后吃的又是什么?以前的生活和现在有什么不一样?解放以前娱乐方式有哪些?都聊些什么?
我奶奶说过去都是吃些红著,红叶菜,好的人家有点米。解放后在五八年大跃进吃大锅饭时,没管饱,大家就自己家下海捞些海鲜接济,因为只有海里出的才是自家的,但以海叶菜为主。讲到现在奶奶很高兴的说,赶上好时候,什么也不用愁。以前最大的娱乐方式就是吃完晚饭,大家一起上沙滩上聊天,天南地北的聊,那是她们最为快乐的时光。
9月11号,早上我带着古老师从祖祠牌坊前的小路出发,参观一片古民居,这里的房子大多是清朝康熙廿十年间建的,所以显的格外的旧,但也显出一份难得的宁静,走在这小路上,古老师的手机就一直没停过,不停地拍,也不停地问关于以前的事。我们随性走进一间小屋,它保存的还算完好,能看出大致的格局,有的房屋甚至连壁橱的门也还在。走过那一间间小屋,就来到了一个地名叫地鼎的地方,传说这就是当年妈祖少时乞鼎砂得筶杯的地方。还记的小时候只要有补鼎的艺人过来,我和小伙伴们就会跟在补鼎人的后面学妈祖小时候对补鼎人喊的那句民谣:“补鼎补铁锅,越补越塌锅”。这个故事上辈人都传的很神,但不知为何历史的书中却没有记载。走着走着就来到我从小居住的古屋前,从外面看,保存完好,可能是因为我奶奶有过来收拾的原由,一切都那么地有条有理,也没长草,看不出是没人居住的痕迹。轻轻的推开大厅的门,儿时的记忆立即涌现而来,时间仿佛定格了,在文革期间藏过妈祖的房间的阁楼里,古老师特地多拍了几张,还不时的问我关于童年的事,走过大厅,走过偏厅还有在倒坍的房屋前,从地基还是可能看出它原来的格局。走过古屋,就来到了古井前,那是一口从宋代就有的井,现还在使用。古老师的手机就没停过,她不停地问我,让我尽可能的回忆起从前的样子。在井边停留一会就继续往古码头的方向走,下了二十三级石梯,来到了位于灵慈东宫左后侧的那口八卦井,此井形状特殊,井口还刻有八卦符号。这是一口位于古码头旁的古井,它的用途就是供来往的船只停泊时汲取的,传说古时此井可供几十艘大船用水,不过现在已没水了。走进灵慈东宫,首先看到的是一对宋代的瓜愣础石柱,灵慈东宫原名天妃宫,妈祖的服饰是红色,为妃时样。宫内除了有顺风耳和千里眼之外,还供奉文曹武判。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灵慈东宫是在1980年按旧址原式重修的,因曾经是作为生产队的队址,所以宫内还保存着从前的样子。2011年在这座旧宫前又新建了一座灵慈东宫,规模比原来的要大4倍左右,耗资600万左右,要在今年的10月16举行开光典礼。走出灵慈东宫,就是长达600米的古码头海岸线,但因妈祖城围海造地,现已看不出来了,只保留了二米左右的一小部分,走上古时的海岸线,就到达了灵慈西宫,它和灵慈东宫处在同一水平面上。宫内的格局也是一样的,只是供奉的神不一样。西宫增加供奉田公元帅,是清康熙复界时部分村民从别处请回来的。但都有千里眼,顺风耳,后殿同样供奉着妈祖。后因灵慈西宫被蛀虫侵蚀再重建,格局才有所改变,但万变不离宗源。
下午我们去了亚奶老太太家,刚好她姐矮古也在,就是一起聊起了妈祖的事,说起从前,留给她们最深的记忆就是文革,游街批斗,口号是“我是大财,一生贪财,藏了妈祖,只为发财”{大财是亚奶的丈夫}但遗憾的是让她们说妈祖的事时,她们不再像以前那样知而不言了,只说了些无关痛痒的小事,说大事妈祖没同意不能说,但说了最多的是卜杯如何灵验的事,古老师很是好奇,问我卜杯的事,我说了这个不是说就能说的清的,她们都有自己的秘诀,没有特定的方式,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图)古教授在亚奶家
9月12号,上午去参观了附近的福慧寺,虽说很是熟悉,但对里面的菩萨大多还是很陌生,还好找了我妈当向导,我当翻译。这真是个学习的过程,下次带别人去就会知道了,不会显的那么无知。在我们参观的时候正好碰到有人过来抽签,古老师就录了下来,还问我抽签的事,我就现学现卖。在参观福慧寺时,古老师发现了几瓶用玻璃瓶装的五色土,旁边还有几袋没装的五色土,古老师说这是值的拍的,这是民间版的,祖祠装的是纪念版的,可以拿回去做一下对比,会更有真实性。福慧寺是在周朝时就有的,中间经历了许多变革,但都幸存了下来。文革时所有的菩萨被毁,但寺院完好的保留了下来〈1952年港里因没有学校,就把它改为了学校,才得以幸存〉。这所学校培育了很多人才,有国家研究员、工程师,还有部队干部等等。现在港里的很多企业家都曾在这里读过书。最近一次的大修建是在08年,花费几百万,重修了寺院,重塑了菩萨,现在置身室内,堂皇的逼人,真可谓金碧辉煌。
下午因老师要找资料,就没出去,后在她的要求下,去找我妈。我妈叫秀梅,她虔信妈祖。也在家里供奉一尊妈祖,这是在平常家很难见到的,不是供奉照片,而是妈祖金身,05年开的光,规模小,但开光程序和祖祠一样,宫名叫“兴圣宫”。对于这个别的案例,古老师表示出莫大的兴趣,问了我妈很多关于开光的事,建兴圣宫的事以及宫内摆设的讲究````。对于有些事,古老师有些不能理解,为什么大家对建寺庙或有关菩萨的事,大家在掏腰包时都是那么的慷慨,这是她所不能理解的。对于卜杯的事,古老师还是不大能清楚,她有那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精神,问我妈很多关于卜杯有事,现在在祖祠里,能卜杯的除了亚奶两姐妹,也就我妈常去了。对于卜杯,我也不是特别懂,这也是我要学习的一部分吧。祖祠厨师秋菊的电话结束了我家之旅。也要六点了,收工。
9月13号,早上在要起程时接了个电话,莆田学院的曾老师也要加入我们的行程,接到电话时,我让他在开元宫会合,紧接着我们也赶赴去了开元宫,长这么大我也第一次去开元宫,对那边我不是很熟悉,但在讲解的时候我还是很自如[早上要出门时我问了奶奶,临时抱了一下佛脚],由于宫门是关着的,所以我们就往下一站接水亭出发了,到了接水亭,正好碰到几个老太太在收拾卫生,在参观完之后,我们就和老太太聊了起来,老太太和我们说了很多关于这所亭的事,很多事我也是第一次听说,特别是说亭曾倒了两次,但有观音的那堵墙就是不倒,听的好灵验啊!怪不得港里辈辈相传这是妈祖父母求佛得子的观音亭。说到兴浓时,又接到祖祠的来电让我们立即回去,说是省电台导演过来,要采访古老师,我们就匆匆了结束这次的谈话,并约了下午还来。回到祖祠时,导演已在那了,在简单的自我介绍过后就切入了访问。我就在一边闲听,这也正是我学习的好机会,导演,教授,还有莆田学院的曾老师,董事长说我好幸运,一来就有机会和这么多学者在一起。想想我真是好幸运,幸运的进入祖祠,幸运的认识这么多好人。最后我带导演一行简单地参观了祖祠、故居、受符井。
(图)古教授在接水亭
下午北岸记者听说台湾来了个古教授,就专程来这边做新闻采访,跟着我们来到了上午没了解完的接水亭,找了那几个老太又闲聊了起来,不过地点改在了贤良港村支部徐先棋的家里,自然也就问了很多有关他家的事了,比方说房什么时候盖的?什么时候出去创的业?启动资金是多少?盖时花了多少钱?接着也问了她们家和这座亭的渊源,还有这座亭所经历的一些事。在无意中,也接触到了民谣这一块,两位老师还有北岸来的林记者对民谣表示了极大的兴趣,都对民谣的发展表示了认可`~~~~~。在结束今天的旅程时,我们特地绕道沿着古时的海岸线[现在的排水沟}往回走。
9月14号,正好福慧寺做法事。早上去祖祠时曾老师已比我们早一步到了福慧寺,参观了法事前的准备工作,我和古教授就随即也去了,简单的参观过后,我和曾老师就去了古民居,〈古教授参观过古民居,就没和我们一起去〉。带着曾老师沿着古路,来到了我从小居住的地方,也就是文革时妈祖藏过身的地方,曾老师表现出和古教授一样的状态,不停的拍,仿佛怕错过什么似的!这在以前是我所不能理解的,但通过这几天的所见所闻,我已能理解了,有了这份心情,我也就有了一份特别的幸福感,为自己生长在这而自豪。出了我家古屋,也顺道去了隔壁几家的房屋去参观了,我也尽量地回忆我儿时的记忆,帮曾老师还原从前的样子。
(图)古教授和曾老师在福慧寺采访老人
离开古民居就又回到了到了福慧寺,法事还没开始,就找了几个老人闲聊了起来,解放前,解放后,天南地北的聊,从中我也得到了很多资讯。法事开始了,古教授用手机记录下了法事的全过程,这也是我最闲的一段时间,这似曾熟悉,但未曾参于的法事让我明白了何为心静。法事做完了,就到了用餐时间,我们一行三人随意找了位置就坐下了,其间有寺董事的工作人员过来,要我们单独找位置坐,但古教授表示没关系,就要和她们一起坐,说这样才更能和她们拉近距离。全素宴我也是今天第一天吃,味道真的不错,呵,既能领略素食风味,又能清理肠胃,真是一举两得。随着餐宴的结束,今天的行程也要随着她们的离去而结束,几天的相处下来,真有点舍不得。都是一行好人,在我刚上手的工作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帮助,妈祖祖姑的恩泽一直庇佑着我,我真是何等的幸运!
注;由于古教授接受莆田学院的邀请,要往莆田学院和市“非遗中心”去参观考察。所以还有许多宫庙和景点没有时间去,如:上港自然村的“开山宫”、“黄氏祠堂”,前头自然村的“钱楼宫”,以及“,风水树”“三柱香”和古代避风港的“港潭里”等地。古教授表示下次有机会再来,一定要把贤良港的古代风貌,民俗风情纪录下来,流传后世。
|